华夏通往贝莱德 焦点速讯
1988年,美国黑石集团旗下一个名为“黑石财富管理”的部门开启了独立运作。
 (资料图)
(资料图)
四年之后,该部门负责人拉里·芬克决定自立门户并更名,经过与黑石掌门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商议,决定沿用黑石的“Black”家族姓氏,将该公司命名为:BlackRock,直译过来正是与黑石集团对应的——“黑岩集团”。
这家初创时仅有8人的资管机构从早年的固定收益起步,并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完成了对巴克莱全球投资者业务(BGI)的收购。
这笔交易总价66亿美元,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一笔巨资,黑岩集团期间还溢价1.5倍击败了出价44亿美元另一家私募机构。
高价并购的原因,正是拉里·芬克看中了BGI旗下用于交易ETF的iShare系统;而此次收购,也让后来的黑岩踩中全球ETF扩张风口,最终跻身了全球资管业的C位。
今日的黑岩集团,在管规模坐拥10万亿美元,已是全球最大的资管平台,国内更习惯将其译作:
贝莱德
海外机构2021年发布的一份全球资管500强名单中,贝莱德排名第1,而国内最大公募易方达排名第77位。
作为仅有30多年历史的年轻机构,贝莱德在华尔街一种资管巨头中杀出重围的关键利器正是在主动岁月的末期,把握住了被动投资崛起的机会。
在境内资管市场,同样孕育着这样一家机构,随着旗下产品线日积月累的复利效应,其发展路径正在成为贝莱德模式在境内的镜像与翻版,它正是“老十家”之一的
华夏基金
范勇宏时代的老华夏,曾是公募基金主动投资能力的集大成体现;如今李一梅治下的新华夏,正在成为被动投资时代的主角。
截至目前,华夏基金旗下已有72只ETF、总规模3000亿元,领先第2名超过1000亿元,市场份额占比达17.7%,已是境内ETF的绝对龙头。
阿尔法机会长期承压的背景下,这个昔日被视为创新业务的冷门产品线,所蕴含的潜在势能,很有可能会沿着成熟市场经验远远超越当下行业的普遍预判。
由于具有较强的工具属性,ETF又有极大概率走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分化格局。
某种意义上,在ETF获得先发优势的华夏基金已提早预定了通往未来“被动时代”的船票。
01
冬天的种子
2005年元宵节午夜,华夏基金负责销售的李一梅只身走在满天飞雪的长安街上。
在一个没有网约车的年代,加班到深夜一旦打不到车只能徒步回家,尽管刚刚从上海飞回北京充满疲惫,但李一梅心中顾念更多的,还是公司刚刚完成上市的境内第一只ETF——
华夏上证50ETF
为了这单无先例的产品创新,华夏基金上下已足足拉扯长达三年。
开发上没有同类案例可参照,只能从道富环球等境外机构处取经;
交易程序上缺乏证券基金有关法律的适用性依据,最终只能在反复论证下寻求特批解决。
打通产品设计、运营、法规体系、系统对接、监管审核等重重关卡后,最难解决的仍然是如何让市场用真金白银来接受这个新事物。
一方面,当时的市场没多少人明白这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产品意义究竟在哪,较高的认知门槛成为推广的重重阻碍。
另一方面,由于ETF属于场内品种,无法得到传统银行渠道的驰援,因此只好找券商施以援手,但一些中小券商本身也一头雾水,李一梅们只好用一次次路演培训,才完成了境内有关ETF产品的最早布道。
在承销机制上,更是引入了类同IPO一样包销模式,18个承销商每家至少领到了2亿元的销售额任务。
然而市场环境也并不友好,启动发行的近一年内,上证50累计下跌已达20%,在预估首发规模时,华夏基金的内部判断是大约20多亿元。
峰回路转的是,经过一连串的路演与推介,这只境内市场首单ETF的首发金额最终居然达到了超预期的
54.4亿元
华夏上证50ETF的发行上市恰好赶在冬季,彼时的资本市场也在经历严寒——其上市时的2月23日,大盘已较上一高点阴跌接近4年,67个交易日之后,上证指数就会触底998点的历史性谷底。
在一个更多人不知ETF为何物的岁月里,华夏上证50ETF的出现,不仅成为了华夏基金布局标准化被动投资工具的开局,更像是冬天里种下的一粒种子,等待在遥远的未来生根发芽。
总有一些早期投入具备长久期特征,不是所有植物在短短三年内就可开花结果,有的需要十年,甚至更久。
02
主动之王转身
和如今占据ETF统治地位不同,华夏基金曾是“主动之王”。
如果回到主动产品当道的10年前,华夏基金在2013年尚以846.9亿元的股基、640.5亿元的混合居于行业之首。
主动规模的优势基本都是过往业绩打下的,华夏最被市场传颂的,则莫过于王亚伟的传奇。
刚刚接手“华夏大盘精选”的2006年,王亚伟就以1.5倍回报跻身股基中的第12位。
07年的6000点牛市中,“华夏大盘精选”净值增长达226%,不仅跑赢大盘1倍多,也问鼎了各路基金收益之首。
在基金新增用户最多的一年拿下冠军,注定会吸纳全市场最多的声量、名利与压力。
而就在全市场注视且指数发生暴跌的2008年,人们开始审视这种业绩能否得到持续时,王亚伟又以较强的回撤控制排列当年基金中的第2位。
王亚伟至此封神,掌管“华夏大盘精选”在6年多时间里,总回报接近12倍,是同类产品平均值的5倍还多。
光环不止属于王亚伟,更早前华夏还涌现出江晖、石波、孙建冬等一批明星经理。
基金业“第一顶流”的打造,不仅让华夏一度尝到规模甜头,站稳行业头把交椅同时,也开启了全行业“打造明星基金经理”的范式。
但明星战术的代价,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12年范勇宏的退居与王亚伟的出走,成为了华夏基金主动时代落幕的前奏。
后来的2015年、2020年两次牛市浪潮中,华夏似乎逐渐失去了主动管理的大王旗,整体规模也纷纷被其他头部赶超。
在行业的不少惯性叙事中,王亚伟后时代的华夏基金,一度被形容为“失去的十年”,因为华夏基金中的顶流经理确实乏善可陈。
然而和许多坐拥顶流的头部机构相比,华夏基金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或许正是
曾经拥有
必须要承认的是,华夏基金比多数管理人更早品尝过王亚伟们带来的主动红利,也足以感知明星出走后对规模冲击的人走茶凉。
如果验证造星模式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复制这种打法尚可以理解。
可一旦在市场突变中被明星效应反噬,此时再不反思固有路径依赖之隐疾,才真正致命。
毕竟没有谁能在年度冠军的王座上天长地久。
近年来顶流不断出圈,造星带量成为行业中的一种复古时尚,华夏基金却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深刻反思而为之的长期阳谋,还是命运使然下欲所不能的偶然结局,已无法得到印证。
但在更多人拼命内卷主动业务之时,华夏却在易被忽视的被动角落围绕ETF产品线长期深耕。
03
不止不休
范勇宏12年卸任后,华夏基金在ETF领域的探索没有结束,其在2013年分别针对消费、金融地产、医药卫生成立了三只行业指数etf;此后又先后围绕恒生指数、MSCI、中证500、创业板指开启试水。
不过华夏基金ETF产品线的真正爆发期,仍然集中在现任CEO李一梅的任内。
2018年5月,前总经理汤晓东离职,李一梅正式挂帅,华夏的ETF产能自此平步青云。
仅在2019年内,华夏新设立的ETF产品就多达8只,其中既包括了日经225等跨境品种,也有5G通信、人工智能等主题,甚至还涵盖了饲料豆粕等商品期货 产品。
此后华夏的ETF更是进入了跑步扩张时代,直到如今旗下ETF数量已达70只余只。
在华夏基金目前的72只ETF中,李一梅任期内成立的多达60只,合计规模接近2000亿,占华夏ETF总规模的
2/3
不得不说,华夏基金重注发力ETF是经过了深度思考的决策。
在2018年的一场投资论坛上,作为演讲者的李一梅直言:
从台下走到台上,只需要一分钟,但华夏基金指数投资,特别是ETF从诞生到作为一种有效的投资工具被大家认可
用了14年
规模结构上,华夏的ETF呈现出宽基、跨境等顺风于市场趋势的特点。
在3000亿的ETF在管规模中,超过一半挂钩了宽基指数;2021年相继设立的恒生科技ETF、恒生中国企业ETF、生物科技ETF等港股产品,让目前的跨境ETF规模占据了总量的近1/4。
尽管一些ETF也成立在牛市的高估值阶段,但挂钩指数的被动工具重要意义恰恰在于——
放弃主动产品高管理费的同时,也降低了主观回撤而引发的声誉风险和赎回压力。
主动产品的亏损或许还能怪罪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但被动投资的责任则却更多反映在持有人的择时上。
何况更多持有ETF的本就是怀揣配置策略下场的机构资金,在风险承受能力上,这部分客户天然强于个人投资者,也有足够认知承受更大的波动。
即便是市场下行的熊市期,ETF也能成为抄底工具,甚至规模变化呈现了与估值走势相背离的奇观。
例如虽然经历了2022年指数大调整,但两市股票类ETF规模已达1.08万亿元,较年初的0.96万亿元还增长了1200亿;2023年至今,该规模进一步增长至1.15万亿元。
熊市中“越跌越买”的现象,正在这个特殊品种身上不断上演。
对于频繁被周期折腾的基金行业来说,ETF无疑表现出了更强的抗周期能力。
04
越来越近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华夏基金的非货规模是7132.3亿元,距离行业第1的易方达至少有3000亿的差距。
但这只是站在眼下的即时格局,是2020年以来主动权益与阿尔法表现持续出圈的结果。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凭借ETF的体量优势,华夏基金的在管规模极大概率仍会不断的
突破行业上限
贝莱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资管龙头,奥秘恰恰在于其利用ETF这把钥匙,冲击了管理规模的天花板。
因为ETF不存在规模上限。
传统主动产品的最大悖论在于:超额收益的创造难度,会随着规模扩大而
边际提升
规模尚小时,投资经理可以通过阿尔法能力斩获优异的成绩单,但每当规模上升一个数量级,维持绩优曲线难度将指数级提升。
这正是不少巨量规模的顶流基金频频出手限购的原因,也是符合有效市场假说且在成熟市场被充分验证的结论。
市场留给聪明资金的最大载客量终究有限。
拉长周期看,随着绩优主动产品的规模扩大,主动乃至量化产品数量的增加,收益曲线最终会向市场共识——指数看齐。
若将交易佣金、更高的管理费纳入考量,主动产品最终“跑不赢指数”就成为一种必然。
这恰恰映衬了巴菲特的预言:长期来看,基金经理无法战胜指数。
全世界都在卷入被动投资的洪流。
截止2021年底的ICI(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显示,被动指数基金占到美股市值的16%,首次超过主动型基金的14%市值规模,而在过去十年中,从主动基金流向被动基金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
主要流向ETF
如果说不受规模束缚、乘风于被动投资或许只是受惠于时代趋势的红利,那么在现有的ETF上形成规模效应,很有可能已成为华夏当下的比较优势。
ETF的规模越大,优势也越大。
因为ETF挂钩指数,投资者无需再将历史业绩、波动性、最大回撤等纳入比较考量,唯一需要判断的就只剩流动性、运营力以及费率等客观要素了。
持有人越多、规模越大的ETF流动性更强,也必然会成为套利、波段、对冲等多策略投资者的首选。
这决定了ETF会像滚雪球一样,具有“先到先得”、“强者愈强”的
商业垄断特质
如此先发优势,从沪深300的ETF格局较量上亦有体现。
全市场沪深300ETF共计23只,其中规模最大的莫过于市场熟知、671亿的华泰柏瑞,而华夏则以246.8亿元居于第2。
华泰柏瑞的长期问鼎,恰恰与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更早设立有关——成立于2012年5月4日的这只产品,是两市首只沪深300ETF。
这只ETF仅比嘉实的同类产品早成立短短3天,但在围绕期指的套利资金涌入下,口含金钥匙出生的华泰柏瑞沪深300ETF便坐拥了329.7亿元规模。
相比之下,成立时间较华泰柏瑞晚了半年的华夏沪深300ETF发行时仅有6亿元规模,尽管如今已追赶至业内第二,但与前者仍然存在接近3倍的差距。
不仅如此,更大规模的ETF也会鼓励市场出现与之挂钩的期权等衍生品,正如近期科创50期权的上市,这将壮大自身生态,进一步巩固不可替代性。
事实上,除了华夏,早已有更多头部发现了这个通往未来产品的秘密,于是在2022年7月,才有了多家头部内卷中证1000ETF的发行大战。
华夏基金在宽基、跨境等ETF上的优势积累,很可能会随着权益市场风格逐渐由主动向被动切换而持续释放。
ETF的发展周期可能会很长,但它会源源不断的释放能量,甚至还能穿越牛熊,对冲市场周期的影响。
ETF的发展速度也可能很快,当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叠加了“中国速度”的Buff,其进化效率往往让人始料未及。
美国从第1只开放式基金到第1只ETF诞生,用了接近70年,中国只用了6年。
华夏上证50ETF的规模从0做到500亿元整整用时长达13年;而科创50ETF做到500亿元规只用了
27个月
18年前的长安街子夜,徒步于漫天飞雪中的李一梅可曾会想到,全公司严冬中辛苦播种的那颗彼时尚不起眼的种子,会在今天成长为华夏基金最深的护城河。
站在当下回看,市场从主动向被动切换似乎已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但回到当初起点,当全行业都在业绩、规模维度拼刺刀,在频繁造星带量之时,默默的长时间布局ETF又是一条何其荆棘且孤独的道路。
正如李一梅的感慨:
我们就像在一条漫长的甬道里往前走,一开始只有若隐若现的微光只有我们孤勇前行,但是现在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加入进来,目前离洞口和耀眼的光
越来越近
某种意义上,华夏的确在重走贝莱德已经走过且验证的路,尽管规模尚有很大差距。
但二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确实更近了。
2020年,贝莱就成立了全资控股的境内公募贝莱德基金。
这家外资机构本土化后的短期成效不甚理想,尽管有华夏基金前任总经理汤晓东的坐镇,但发行的6只公募产品中有5只至今浮亏,其中规模最大的贝莱德中国新视野回撤超过30%。
6月6日,作为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的汤晓东提出辞职,结束了其在贝莱德的4年任职生涯。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
从华夏离开的汤晓东,未能让入华后的贝莱德复刻华夏的荣耀;李一梅执掌期的华夏,却正在通往贝莱德的路上越来越近。
(完)
风险提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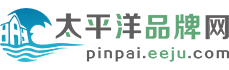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相关新闻